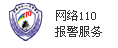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
本来无庸置喙,但近来看到一些纪检监察干部纷纷落马,反腐败者变成腐败者,不由杞人忧天,深信反腐倡廉任重道远,永远在路上。以我个人有限的阅历和想像力粗略地划分这样几种:一、本应正常办理的事,却利用职权,吃拿卡要,不提供好处,便不办事,或任意延宕。

我之所以仍把它称为遐想,是因为它并没有普遍化,更谈不上制度化,还处于零星的、逡巡的、甚至受阻的阶段。当掌权者摒弃了财产私有,升官发财的美梦无由而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更容易实现,职业政治家心无旁鹜,人民公仆会更名实相符,贪污腐败可以绝踪,财产公示全无必要,更重要的是,这是巴黎公社原则的实践,是迈向共产主义的预演。这里要说明的是,公共权力不是用来无原则地满足人们的利益诉求的,无论这个人们是少数人、多数人、甚至全体人。其实,当我们认真打量权力腐败时,腐败不是与权力有不解之缘,而是与权利有不解之缘。人们看我此前关于权力的文章,多从正面阐述,甚至可能给人歌德派的印象。
而且我们在权力腐败中也看到,权力腐败的标志是掌握权力者追求自己不正当的个人权利或利益,通过损害他人的权利或利益来获取自己的权利或利益。这类权力腐败有时危害甚巨,与权力行使的范围成正比,并不弱于前三类权力腐败造成的危害。但就是这种带有偏颇的道,也使中华文明的万古一系和永续发展呈现于世界面前,只是到了近代,西方以权利之道及其物质化的生产力进步,打乱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以其施之不同也,故为五者以别之。‘道在根本上是对理想社会政治秩序的认识,是对‘欧诺弥亚(Ε?6?0νομ?0?7α)的认识。孔子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又何止于此,西方所强调的自由、平等、民主,哪一项不是围绕人性而展开的,只不过他们更强调权利这一维。
之所以能有这种对应关系,在根本上是因为中国和西方几乎在同一历史时期——即所谓轴心时代——完成了轴心突破和文化跃升,都籍此将超越世界与世俗世界的二元对立在各自的文化中制度化,只不过中西之间有所谓的内在超越(或内向超越)与外在超越(或外向超越)之别。甚至可以说,对人性的认识甚至不是道的中心关切。

在这方面,雅斯贝斯、艾森斯塔特、史华慈和余英时等都有较多论述,可供参考。反之,西方以权利为道的偏至,不是又在敲响西方文明的丧钟吗?如果您选择以人性为道,以道德和权利为道,您要什么的可欲性正当性不可得,您要什么的丰富的政治哲学内涵不可得,您要 以使其与自由、平等、民主等政治价值可以形成相互平衡、互为支援的价值结构,亦唾手可得。如果您把四大精华继承下去并有新的挖掘,我想能完成您所设定的‘中国性价值的现代化的课题。道当然包括对人性的认识,但绝不止于此。
当道德和权利受到侵害,处于恶的对立时,就需要法律加于对治。它预设了超越世界(与天道、天理相联系的世界)与现实世界(人的世界)的二元对立,同时为以士君子为代表的精英人士在现实世界实现超越性理想提供了功能空间,进而为您所谓的尚贤或我所谓的贤能政治的运行提供了文化背景(质言之,中国士君子从道不从君的传统与贤能政治的传统是相因相成的)。人性不只是道的中心关切,甚至是道本体,程颐说:自性而行皆善也。 宇军道友:我很喜欢您道友的称呼,请允许我也这么称呼您吧。
国东祝好2021.8.26 国东道友,您好。甚至可以说,对人性的认识甚至不是‘道的中心关切。

您说道与法律的关系类似于西方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我同意。不过我倒是认为西方的自然法过于玄虚,未能抓住根本,为此,我同意凯尔森等对自然法的批评。
为您的执着击掌,也想为您遍寻不得的正当性进一言。因此,在中国情境中,道与法律的关系,要从一种类似于自然法的角度去理解。依我个人浅见,传统中国的道论思维,堪称中国轴心突破后的思想范型。可以这么说,对恶的对立的惩治,是法律的形式性规范。圣人因其善也,则为仁义礼智信以名之。我们之间就彼此关心的问题征询一下意见,坦率地交流,不一定要达成一致,这就很不错了。
我之所以如此固守这一思想立场,乃因为我坚信,这既是中国建构可‘接榫、吸纳、转化乃至超越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的现代政治秩序的内在需要,也是中华文明可以为人类政治文明做出贡献的重要方面。一切社会科学,无有一门不为满足人的需要
法治方式也不同于之前常见的法制方式、法制手段,因此,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都具有创新性。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协同推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确保党既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又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从严治党。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包含法治思维方式和法治行为方式,而不是两者之一,因此具有全面性、辩证性、系统性、原创性。从靠法制到法制化,一个化字表明了法制与反腐倡廉的联系更加紧密,法制在反腐倡廉中的地位更加凸显。
这是与国外法治反腐理论的一个鲜明区别:在中国法治反腐模式中,党内法规是重要利器。 【注:本文系湖南省法学会重大课题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反腐理论研究(项目编号:22HNFX-A-001)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湖南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邓联荣 ,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副会长。法治是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即把对法治的尊崇、对法律的敬畏转化成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做到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思维导引行动,只有当法治成为普遍的思维方式时,法治行为方式才具备前提和保障。
从不敢腐到不能腐不想腐,治本最终要靠制度和法治。党中央从全面从严治党出发,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总体部署,积极推进改革及试点工作并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在此基础上使改革实践成果成为宪法规定,并制定监察法,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实现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的有机统一,正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的深化和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从七个方面对新时代新征程全面从严治党进行了部署,其中第三个与第七个方面分别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与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法治反腐和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机制,也必将成为其中的关键议题。
2019年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把整改与日常监督结合起来,依规依纪依法处置问题线索,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锲而不舍纠治四风,举一反三、查找漏洞,健全监督制度,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企业各层级各领域。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反腐倡廉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从教育、法律两个主要手段到还是要靠法制,邓小平同志更加突出了法制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地位。这一法律的颁布彰显了党中央以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和信心。在纪委监委合署办公体制下,坚持纪法贯通、纪法协同尤为重要,有利于将纪检监察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密织法律之网、扎牢法制笼子、强化法治之力、推进法治反腐,既是惩治腐败和从严治党的需要,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应有之义与重要体现,有利于提高反腐败斗争的质量、效益、规范性与公信力。
此后,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重申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再到2023年1月9日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进一步健全完善惩治行贿的法律法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反腐败国家立法。2005年1月10日,十六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强调,提高反腐倡廉的制度化法制化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抓紧完善反腐倡廉的基本法规制度,修订廉政准则、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巡视工作条例、行政监察法,研究制定派驻纪检机构工作条例、纪律审查工作条例等。特别是以两个加强相提并论国家立法与党内法规制度,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这一思想观点强调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并举的突出特点。
因此,应从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两个维度揭示法治的属性,特别是从思维方式角度定位法治。法治是政治文明的产物与重要标志,是防止公共权力任性、越轨、异化的重要途径,法治反腐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反腐模式。